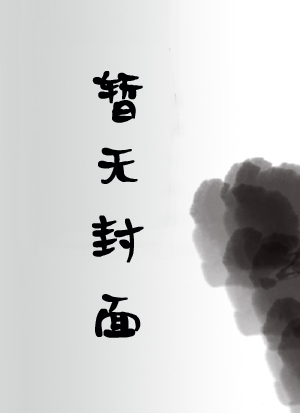常歲甯将那張信紙展開來看,隻見上書幾人姓名,籍貫,履曆,甚是詳盡。
「他們三人皆為我少時同窗或昔日好友,雖各有優缺長短,但皆是真才實幹之輩,各自于所擅之項皆能獨當一面。」駱觀臨道:「若能說服他們前來江都效力,于大人定能有所助益。」
見常歲甯隻看着那信紙不語,駱觀臨擰了下眉:「大人是覺得哪裡不妥嗎?」
常歲甯适才擡起眼睛,看向他:「我隻是未曾想到先生竟這般為我思慮周全,一時很是觸動。」
駱觀臨将手負起在身後:「……大人不必過于誤解,駱某這麼做,也是為了向江都贖罪。」
公事歸公事,别同他扯這些,自徐正業之事後,他已封心立誓,此生絕不會再同這些表裡不一的野心勃勃之輩談什麼感情了……同樣的錯,他定不會再犯第二次!
「先生待江都之心,我都明白。」常歲甯道:「先生是不忍見我這座刺史府裡如今大半都是青瓜蛋子,故而才會與我舉薦能才,以解我與江都燃眉之急。」
「豈止是青瓜蛋子……」駱觀臨想到被委以重任的沈三貓等人,嗤道:「還盡是些奇形怪相的瓜蛋子。」
這話常歲甯并不贊成,瓜這種東西,長得怪,不代表它不甜呐。
但她此時手裡攥着人家的好意呢,她也不好同人擡杠,這位駱先生是這樣的,為人自傲,性情尖銳,眼裡揉不得半粒沙子,輕易不喜變通,但用人便是如此,看中了人家的長處,就要包容對方的不足。
誰讓她如今手底下缺人缺得厲害呢,若非她拿着軍功唬人,加上王長史是老師安排的人,從一開始便與她同心協力,她在這毫無基礎的江都想要推行諸事,遠要比現下更難。
縱是如此,她還每日累得沒時間吃飯睡覺呢,歸根結底,還是因為她手中沒有一個構架完整成熟的班底——
這便注定了一點,她想要跟從江都官員的意見,一切聽之任之,中規中矩行事尚可,但當她一旦想要按照她自己的意願施行策令時,凡事便必須她親力親為。
不巧的是,她從一開始便打定了主意要讓江都按照她的意願重建,且她不打算讓自己成為一個權職被半架空的空殼刺史。
所以這段時日便隻能累得昏天暗地。
她知道,駱觀臨瞧不上沈三貓、何武虎之流,甚至也不大瞧得上姚冉和呂秀才,因為他自認學識才幹過人,縱一時落魄了,但他是為正經進士出身,曾任京官禦史,資曆遠非常人可比——
常歲甯也覺得對方這幅目中無人的模樣很欠收拾,但同時她又不得不承認,對方是很有一些值得自傲的本領在的,那些為官的資曆與見識,放在别處或軍營中,或是無用物,但在江都政事之上,卻是寶貴實用的。
欲治理一州,絕非一人之力可以達成。
縱觀成大事者,身側相助之人,又豈會盡是同一類人,世人原本皆是性情各異,各有長短的。
因而,将人擺在合适的位置上,讓對方的長處充分發揮,是于她而言最實用的選擇,至于那些個人小小性情,相較之下不值一提。
眼下對方不就已經開始發揮長處了嗎?
就「瓜」這個話題之上,常歲甯接過話,點頭贊美道:「論起咱們刺史府的瓜來,就數先生長得最是圓咚咚,且個大标緻,堪稱瓜中諸葛,瓜田之首。」
駱觀臨嘴角胡須抽動了一下:「……常刺史這是誇人?」
「當然。」常歲甯笑微微地晃了晃那張信紙:「且先生又幫我拉了這些同樣标緻的好瓜來,我都不知該如何感激先生才好了。」
「八字才隻一撇而已……」駱觀臨道:「駱某隻是将這些可用之人推薦給刺
史,接下來還須刺史一一去信說服。」
「那依先生之見,我要如何才能勸服他們呢?」常歲甯請教着問。
「他們各自經曆不同,或是對當今朝政不滿,遲遲不願出仕,或是遭異己打壓難展才幹……但無一不是昔日心懷抱負之人。」
駱觀臨道:「眼下時值紛亂,他們的處境也不免艱難,既難獨善其身,便總要有所抉擇,才能庇護家人。而現下江都興建學館,優待有識之士的美名已經傳揚出去,隻要常刺史誠心相請相待,便是很有希望說動他們的。」
常歲甯先是點頭,思索片刻後,卻又道:「先生所言在理,但我有個更易成事的法子。」
「我與這幾位先生素昧平生,貿然去信,他們免不了觀望遲疑一番,若是這期間他們被當地豪強或其他藩王強召了去,那就不妙了。」
常歲甯說着,看向駱觀臨,一笑:「先生幫人幫到底,這信不如就由先生出面來寫吧。一則,先生與他們交好,情分在此,先生的話更有說服力。二則,先生更了解他們各人的性情忌諱,更可對症下藥。」
她越說越覺得可行:「到時由先生為我之人品德行作保,此事何愁不成?」
駱觀臨眉心一跳:「常刺史莫不是忘了駱某已是個死人了?死人如何去信?」
常歲甯:「這便是最妙之處了——」
死人來信,何其刺激?
「先生您想啊,倘若您已知舊友過世,卻忽然得舊友來信,知曉舊友死而複生,怎能按捺得住一探究竟的心情?」常歲甯道:「如此奇事,若換作我,即便我明日成親,必也要連夜收拾包袱前去一觀。」
駱觀臨:「……」
親都不成了,那她湊熱鬧的瘾還怪大的!
但想想……也是這個理。
死而複生這種熱鬧,非尋常熱鬧可比,誰又能視若無睹呢?
常歲甯又勸:「橫豎待他們來江都後,遲早也是要與先生相認的,不如就辛苦先生提早死而複生一下吧。」
駱觀臨考慮了片刻,雖說他易主的經曆相當丢人,但咬咬牙,也無甚不敢相認的,隻是……
「我怕他們此刻或已有欲投效之人,見我信後,若将我尚且在世的消息傳揚出去,便會讓你背上窩藏反賊的罪名。」駱觀臨遲疑着道。
雖是舊友,卻也有背刺的可能。
常歲甯并不在意:「無妨,無憑無據之事,朝廷到時隻管讓人來江都搜便是了,搜不到先生,自然便定不了我的罪。」
駱觀臨擰眉又思索了一會兒,到底是道:「麻煩還是能免則免。不如這樣,可由我來寫信,但信上隻邀他們前來江都秘密相叙,暫時不提我如今的處境,及你之名号。」
「餘下的,待他們來到江都之後,再當面詳談便是。」
駱觀臨道:「如此一來,他們縱然有揭發我的想法,卻也牽扯不到你身上來。且待他們入江都後,一切便在你掌控之内了。」
常歲甯沉默了一下,才道:「先生不單缜密,還事事皆為我着想——」
駱觀臨:「……」
都說了在其位謀其政!
又聽那少女緊接着說道:「由此可見,我做事做人很是可以。」
駱觀臨猝不及防之下被閃了一下:「?」
怎麼就能誇到自己身上去的?
「先生,我此前沒說大話吧。」常歲甯笑着道:「與先生初見時,我便與先生說過,我的優點很多的,我不單擅長殺人,在其它方面也稱得上天賦異禀——先生如今相信了吧?」
駱觀臨嗤笑道:「……常刺史最大的優點便是從不謙虛。」
常歲甯輕
點頭:「天賦異禀,很難謙虛。」
駱觀臨還欲再嗆她兩句,隻聽她已接着說起正事:「既如此,那便依先生所言,由先生先将人哄來……不,是請來江都做客,到時我定好生招待。」
看着面前少女好客的笑臉,聽得這好生招待四字,駱觀臨腦海中最先浮現的且不是鴻門宴三字,而是……全麻宴。
——全是麻袋的那種有來無回宴!
此一刻,駱觀臨心底蓦地生出幾分悔意,但轉念一想舊友們此刻朝不保夕的處境,又覺得相比之下,被常歲甯裝進麻袋裡,也沒什麼不好的……
隻是心底還是不免生出幾分充當人販子的微妙感受。
這種感受因為常歲甯接下來的話,而變得更為強烈——
敲定此事後,常歲甯又說起被糾錯塗改的藏書抄本,說明日還會有一些送回來,到時讓他先挑,大可多挑幾冊。
駱觀臨沉默不語,腦海中浮現八字——賣友求書,多賣多得。
常歲甯坐回自己的位置後,又随口感歎道:「……先生願意将這些舊友引薦于我,而非徐正業,可見先生待我之心,已遠勝過昔日待徐正業。」
駱觀臨很是看不得她這幅自得的模樣,不冷不熱地道:「也向徐正業引薦過,隻是彼時前去投奔徐正業者甚多,他未有十分放在心上罷了。」
常歲甯「噢」了一聲,卻也沒有自作多情的尴尬與羞愧,而是道:「可見徐正業并非伯樂,他們與徐正業注定無緣,唯有與我才是天定的緣分,正如我與先生這般。」
駱觀臨:「……刺史大人這張嘴還真是應對自如,從不令自己陷入被動之地。」
常歲甯一笑:「先生慧眼,很擅長發現我的優點。」
駱觀臨嗤笑兩聲,不再與她做口舌之争,但心中卻又不得不承認,這個看似滿嘴诳語的少年女郎,城府遠比表面看來要深。
她從不對他有半分厲色,無論他言辭如何刻薄,她都總能以玩笑化解,避免與他争執的同時,又不會讓話題偏離她的掌控……起初他尚且不以為意,但随着相處久了,卻不免逐漸意識到,單是此一點,便不是尋常人能夠做得到的。
在他面前,她簡直像是個沒有半點脾氣的人。
可事實果真如此嗎?
他并非沒見過她提刀的模樣,甚至徐正業的頭顱就是她親自斬下的。
她絕不是個真正意義上好脾氣的人,但她卻能做到長久地維持住這幅好脾氣的面孔與心态,時常叫人根本分不清真假……這份自如的掌控力,便是當初的徐正業也做不到,說是他平生僅見亦不為過。
他時常覺得她根本不像是一個十七歲的女郎。
若說經曆造就不出這樣的她,那麼便隻能用天生奇才來解釋了。
這些時日所見,駱觀臨已不得不承認,這的确是一位罕見的少年奇才。
她來江都,不是任性胡鬧,一時起意,她是在認真紮實地做事,雖然她的舉措往往帶有濃重的個人色彩,卻又皆能如她所言——她無愧江都。
也是因此,他才會下定決心舉薦那些亟需安身之處的舊友。
無論如何,至少他當真從此時的江都身上看到了安定的希望,哪怕它甚至正在被倭寇觊觎着。
如今大盛渾身上下哪一處,又是不被虎狼觊觎着的呢?
至少江都有她和常大将軍願以性命鎮守。
想着這些,駱觀臨也沒了同常歲甯繼續嗆聲的心思,他主動問起正事實務,提到正在修建的學館時,又說到了對沈三貓此人的不放心。
常歲甯卻笃定地道:「先生放心,建個學館而已,沈三貓定能辦得好此事。」
又道:「況且,他是最能替我省銀子的。」
見她用人之心甚堅,駱觀臨也不好再說什麼,隻是聽她說到省銀子,免不了要問一句:「……大人果真有足夠的銀錢建成這座學館?」
常歲甯:「眼下是先拿我阿爹的家底墊用着的,若将我阿爹的養老銀子掏空,應當差不多夠用。」
聽得這傾家蕩産之言,駱觀臨沉默下來,畢竟他沒錢幫忙。
他隻能道:「照刺史這般行事,後續要用錢的地方隻多不少,還當早做些打算。」
常歲甯認可地點頭,她是怪敗家的。
開源之事她已有打算,但前期也還須本錢去撬動,老常的養老銀子她也得想法子補回去才行……
窮到家的常歲甯想了想,覺得是時候給孟列寫一封信了。
雖然她拿不準孟列此刻的心思,但設法将她之前在登泰樓的「私房錢」拿回一半,應當還是行得通的。
當晚,常歲甯寫了一封簡短的信,讓人送回京師,與那封信一同被送回去的,還有那半枚舊日令牌——讓人送出去的那一刻,常歲甯在想,這麼多年了,另一半令牌,倒不知孟列還有沒有留着了。不過他記性好,定然是能夠認得出來的。
但常歲甯沒想到的是,在得到孟列的回音之前,突然有人送了一筆錢到她面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