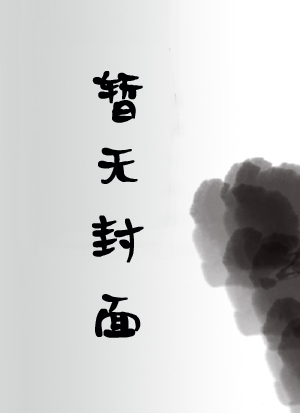第872章 祥瑞頻出
秋落霜見他出去,這才鬆了一口氣,拉著秋長歌的手問道:「昨夜過的如何,大公子沒有為難你吧?」
她不用問也知曉,就剛才大公子那模樣,定然是讓七娘吃了大苦。
秋長歌搖頭:「無事,他不敢為難我。」
秋落霜哪裡肯信,說道:「雖說咱們女子是依附男子而活的,七娘你日後全指著他過活,但是你身體弱,該拒絕的時候就一定要拒絕,若是年紀輕輕壞了身子,日後就不好調養了。」
秋長歌點頭,她也不全指著蕭霽過活呢。
「我知曉了,姑母,蕭霽也就休沐三日,後面定然是要忙著不著家的。」
秋落霜:「這不著家也不成啊。」
秋長歌笑道:「是是是,姑母就留下一起用晚膳吧,新來了一個會做飯的嬤嬤,做的飯菜很是可口。」
秋落霜被她帶偏了話題,於是就留下來一起用晚膳。
晚膳時,她見蕭霽吃飯不言不語,一個勁地給七娘夾菜,見她喜歡吃什麼,就多夾兩筷子,見她要吃茶便給她倒茶,完全不像個當家的郎君,心中又驚又喜又困惑,覺得這樣應該是好事。
秋落霜用完晚膳就被蕭霽尋了個由頭送回了憐花苑,等回去才跺腳,想起自己還忘了叮囑很多事情。
「今日你何故急著送走姑母?她都被你嚇到了。」秋長歌自是將一切看在眼裡,等人走了才發作。
蕭霽「哦」了一聲,說道:「你姑母說話聲音太大,我在外間都聽到了。」
秋長歌氣笑了:「你確定不是故意偷聽的。」
蕭霽抿唇:「那不能,我隻是耳朵比一般人靈敏。不過你姑母說的沒錯,日後我會知曉節制的,在你身體調養的和普通人一樣之前。」
言下之意,一旦她身體調養的和普通人一樣,他也就不用節制,而是無所顧慮了。
秋長歌:「……」
她不太想和他討論這個話題。她覺得體弱一些也是有好處的。
「公子,該喝葯了。」雪鴞端了一碗漆黑的葯過來。
秋長歌見雪鴞表情古怪,放下藥碗,飛奔就跑了,眯眼道:「什麼葯?」
蕭霽面不改色道:「避子葯,我喝的。」
她的身體先天受損,不易受孕,但是蕭霽還是為保萬一,讓碧霄配了避子葯,他皮糙肉厚的,他來服用,這樣於她身體無害。
秋長歌愣住:「昨夜你也喝了?」
蕭霽點頭:「自然。」
說著他仰頭將碗裡的葯喝的一滴不剩。
秋長歌:「……」
那為何他今日還要喝?
蕭霽鳳眼灼灼地看她。
那求偶的眼神,瞬間就讓她頭皮發麻起來。
蕭霽:「我隻休沐三日,三日後估計每日深夜才能回來。」
秋長歌「哦」了一聲,沒有反應。
蕭霽:「你不問問我為何回來這麼晚?」
秋長歌懶洋洋道:「左不過有你要做的事情。」
她懶得問。
蕭霽心情有些不太好,若是他每日半夜才回來,那豈不是不知道她白日做什麼,見什麼人?也見不到她?
成了親還不能時時刻刻見到人,也真是夠憋屈的。
隻是想起朝堂上的事情,他鳳眼幽深,說道:「陛下有意給六皇子和鎮國公府的孫娘子賜婚。」
鎮國公府是有兵權的。這也是六皇子一時心心念念要娶孫娘子的原因。
想起道觀一事,蕭霽眼底閃過一絲冷意,如今老,這天下江山就差一步就在他手了。
若是讓他上位,日後還不知道要做出什麼荒唐事來。
為儲君之位娶鎮國公府的小娘子,為美色深夜派人強擄小娘子,這等目無王法、肆意妄為的皇子,還真是令人生厭啊。
秋長歌:「鎮國公府有兵?」
蕭霽點頭。
秋長歌輕笑了一聲:「這走的不是尋常路呀。不走清流這一派,走的竟然是兵權,他想做什麼?」
蕭霽鳳眼瞬間亮了起來,低沉笑出聲來,笑聲愉悅,和她說話,總是會有意想不到的收穫。
蕭霽:「我會盡量每晚早點回來。」
如今時局動蕩,他不能一味地沉浸在兒女情長中,等日後,報了道觀之仇,報了他的皿海深仇,他們有的是時間在一起。
蕭霽已經開始暢想未來,與她在一起,就算當個教書匠或者當個殺豬賣肉的,好像都不錯。
秋長歌點頭:「嗯。」
「我不在家的時候,你不要單獨見老二和老四,就算有別人陪同也不行。」蕭霽說的是立女戶那日,她在酒樓和蕭茗、蕭宣一起吃飯的事情。
秋長歌嗤笑一聲,果然心眼比針還小,就說他沒那麼大方,這麼久的事情還拿出來說嘴。
蕭霽見她漫不經心地點頭,有些惱怒,起身將她抱起來:「天色不早,我們還是早早安置了吧。」
秋長歌:「……」
三日休沐,休沐結束之後,蕭霽就恢復了忙碌的日常。秋長歌早上起得晚,每次起床,他都已經走了,於是大多自己一人用早膳,有時候夜間被他鬧的厲害,午時才起,就索性直接用午膳。
蕭霽不在家的時候,她不是看看書打發時間,就去秋落霜那邊坐一坐,偶爾也去清風堂和蕭公一起下棋,去衡安齋陪老夫人喝茶看戲。
自打蕭公知曉她會下棋,下了一盤之後,兩人就成了棋友。
一時之間,內宅都隱隱側目,於是府中上下都開始學棋,就連秋落霜那裡都擺了一個棋盤。
秋長歌有些瞠目結舌,不過也樂見其成。
蕭公的棋藝,有點不好說,就是俗話中的臭棋簍子,越菜越愛玩,秋長歌讓他幾個子,都能贏。以前老太爺藏著掖著,不肯讓人知曉,後來和她下了一盤,下出了棋癮來,便隔三差五地要下一盤。
秋長歌自然巴不得滿府都會下棋,這樣蕭公也不用逮著她一個薅,自是有人陪他下棋。
這事自然而然就傳到了蕭霽耳中。
夜裡蕭霽咬著她的耳朵問道:「聽說,你現在和祖父是忘年交,每次下棋都殺的祖父片甲不留?」
秋長歌不耐煩地翻身背對他,近來他一身使不完的力氣,還不讓人睡覺,於是冷冷說道:「殺一次,至少三日蕭公不敢找我下棋。」
蕭霽低低地笑,他娶的小娘子真是心硬如鐵,偏偏他喜歡的不行。祖父那棋藝,蕭宣都避之不及,也就她不知道,被祖父知道了她會下棋,本以為是個旗鼓相當的,結果遇到了一個殺神。
這幾日祖父長籲短嘆,不知道的還以為朝堂發生了什麼大事。
不過朝堂上也確實該有大事發生了。
「近來,禦史台聯名,奏請陛下封六皇子為儲君。」蕭霽抱著她香香軟軟的身子,在她耳邊說著朝堂大事。
秋長歌半睡半醒間,含糊地說道:「陛下不裝模作樣找先太子了嗎?」
蕭霽愛極了她這淬了毒的小嘴,將她翻了過來,抱入懷裡,肆意親吻一番,說道:「可能是裝了十多年,不想再裝了。」
秋長歌抵著他寬厚炙熱的兇膛,昏昏欲睡中。
「不過世事豈能盡如人願。」蕭霽冷笑,鳳眼冰冷,低頭看去,隻見她已經貼著他的兇口睡著了。
他伸手摩挲著她的髮絲,將她抱的更緊了一些,低語道:「不如我為你打下這江山吧。」
*
五月裡,六皇子和鎮國公府聯姻,娶了孫娘子。
成親第二日,老鎮國公奏請陛下,立六皇子為儲君,蕭公未表態,除了禦史台,百官見蕭公不表態,俱是不言語。
陛下回憶往昔被先帝立為儲君的那些歲月,淚灑朝堂,駁回了老鎮國公的奏請,說還想努力一把,尋一尋先太子,將皇位還給先帝一脈。
於是儲君一事暫時擱置。
不過此事一旦被提起了頭,後續立儲君不過是早晚的事情,滿朝文武誰人不知曉,先太子早就命喪火海,陛下不過是為了史書清名,假意推脫罷了。
端午來臨之際,盛京卻頻頻發生怪事。
「聽說最近盛京河裡每到傍晚時分,便有成群結隊的魚兒躍出水面,還有漁夫捕撈出這麼大的魚。」
水榭廳內,蕭璧眉飛色舞地說著最近的奇事:「那魚有一米多長,本也不是什麼稀奇之事,最稀奇的是魚肚子裡藏了一塊龜甲,上面寫著聖人臨的字樣,我朝最是崇尚聖儒,這一下大家都在議論紛紛,說是不是天降預警,儲君人選要定了。」
二夫人見他說的唾沫星飛濺,笑道:「你可別胡說八道吧,凈撿了外面不入流的小道消息回來唬我們。如今陛下膝下能繼承皇位的就一個六皇子,這龜甲乾脆寫六皇子名字算了。」
眾人掩口笑,滿堂都是歡笑聲。
可不是,乾脆寫六皇子名字算了,省得猜來猜去的。
秋長歌坐在四夫人下首,也跟著微微笑。
蕭璧急道:「娘,你聽我說完,這事若是指的是六皇子,那我還拿回來說做什麼,這隻是一樁怪事,還有呢。」
眾人奇道:「還有?」
蕭宣見他這副嘩眾取寵的模樣,偏偏家中的祖母和嬸娘都吃他這一套,頓時冷笑道:「不過是使了一些手段罷了。那龜甲定然是被人縫進魚肚子裡的,難不成魚還能吃龜?魚能活多久,龜能活多久?」
眾人暗暗點頭,是這樣沒錯,但是百姓可不會追根溯源,他們連事情始末都可能不聽清楚,隻會求結果,然後一傳十,十傳百,然後傳的久了,就全都信了。
蕭璧:「老四,你別說話。這第二樁怪事就是京郊一處廢棄的琉璃廠突然天降大火,那日好多人都瞧見了,那火直接沖著琉璃廠而去,燒了一夜了,第二日有人在土裡翻出了沒燒毀的瓷罐,上面寫著十年生死無人知,一朝火起天下聞。」
老夫人詫異道:「這是何意?」
秋長歌垂眸,雕蟲小技,痕迹太重,但是爍口成金,有些時候不問真假,隻是需要一個由頭,便能將塵封的舊案盡數翻起來。
幾位夫人也不明所以,蕭宣不說話,今年的春闈科考,他本想參加,但是被二哥攔住了,二哥說,明年再考。
科考三年一次,明年怎麼能再考?不過他一向敬重兄長,沒有問緣由,直接就棄考了。為此再等三年又何妨?
聯想到近期發生的這些怪事,蕭宣隱隱意識到了那要來的風雨。
蕭璧跺腳道:「你們真的想不到嗎?七娘,你來說。」
眾人紛紛看向秋長歌。自打秋長歌入府,老太爺對她很是看重,這女娘既不掐尖也不冒頭,平日裡除了有些懶散,也沒有什麼缺點,既能陪老太爺下棋,也能陪老夫人聽戲,幾位夫人為了那點子內宅之權鬥的烏雞眼似的,她都能悠閑地喝茶,全然一副不關她事的姿態,到最後,幾位夫人若是遇到爭執的事情,全都找她來評理。
偏偏她每次都能給出完美的解決方案,讓所有人都心服口服。
短短兩月,蕭府上下都喜歡這個躲懶的小娘子,每次宴會誰都可以不請,必要請她,就愛看她一副躲懶又不得不來的樣子。
秋長歌見眾人都看著她,淡淡嘆氣道:「十年生死無人知,一朝火起天下聞,聖人臨。」
眾人大吃一驚,原是要將這兩件事情聯繫在一起來看,這,這可是不能說的大事。
老夫人不禁想起十多年前的那樁慘案,那時別說宮廷,整個盛京都皿流成河,家家戶戶閉緊門窗,不敢伸頭,大火燒了三天三夜才停歇,先帝駕崩,龍椅上換人坐,改朝也換代了。
這才多少年,就又要掀起新的風浪了嗎?
四夫人有些後知後覺道:「不是指六皇子,那是指何人?」
蕭璧神神秘秘地說道:「現在外面好多人傳,說是那位沒死。」
「哪位?」四夫人見眾人諱莫如深的模樣,急道,「七娘,你來說。」
這些人真是,藏藏掖掖的,一向都是有話不直說,她要是知道,還會問嗎?能不能學學七娘,每次有什麼就說什麼,從來都不帶怕的。
秋長歌輕咳了一聲,淡淡說道:「應該是說先帝的那位小太子,當年他便是火場喪生的,陛下這些年不是一直在尋嗎?萬一沒死呢?」
自然是沒死的,早就被蕭公藏在府中養大,如今還日日睡在她身邊呢。隻是她沒有想到,蕭霽動作這麼快,竟然想奪陛下的皇位。這果然是當今陛下的死穴。
水榭廳頓時倒吸一口涼氣,真的是那位沒死嗎?
老夫人威嚴道:「這種話家裡說說也就算了,萬不可在外和那些人一起渾說。」
眾人連忙應道:「是,老夫人。」
因這一樁事,大家晚膳吃的都有些心不在焉,不知道真假,但是無風不起浪,若是先太子真的沒死,那就是。
陛下這些年來,日日都打感情牌,如今正主回來了,這皇位讓還是不讓呢?
用完晚膳,眾人便起身告辭,各回各家。
雖是五月裡,但是夜裡還是有一些涼意,秋長歌打著團扇,帶著梅香回心齋,一邊走,一邊問道:「大公子還未回來嗎?」
她已經兩日沒見到蕭霽了,這兩日,蕭霽都是深夜才回,她還沒睡醒,對方又走了,今日聽了蕭璧那些話,才知曉原來他最近忙的是這一樁事情。
梅香說道:「今日我問雪鴞,雪鴞說大公子不一定能回來。娘子,這一天天的真的有那麼忙嗎?這都不著家了,娘子,萬一大公子在外面有別的相好呢,你怎麼也不著急。」
秋長歌似笑非笑道:「那正好,和離了還能再尋一個。」
蕭霽能有什麼相好的小娘子,自打成親以來,若非她身子弱,隻怕要被他鎖在床上了,她隻盼著他能更忙一些,她也好輕鬆一些。
這幾日就很輕鬆。白日裡吃吃喝喝看看書,聽聽八卦,夜裡一個人睡的很是清爽自在,不用貼著一個火爐了。
「嫂嫂這話若是被蕭霽聽到了,怕是要鬧的家宅不寧了。」蕭宣陰柔的聲音從後面傳來。
秋長歌回頭,看見他,淡淡說道:「隻是玩笑話,四弟這是去哪裡?」
「去二哥那裡借幾本書,正好順路。」
秋長歌點頭,自從她買了三夫人的宅子,嫁入蕭府以後,蕭宣倒是真的恪守禮數,見面都喚她嫂嫂,所以秋長歌對他也有了改觀。
「四弟今年不是要參加春闈科考嗎?為何沒去?」
蕭宣有些意外:「七娘也知道此事?本是要參加的,結果那日鬧肚子就沒去成。」
秋長歌微笑:「聽三夫人提了一嘴,下次再考也是一樣的。」
若是改朝換代,今年考,確實不如明年考。一朝天子一朝臣,當權者的心腹必然是自己精心挑選出來的。看來蕭氏是徹底站在了蕭霽這一邊。
蕭宣見她言辭之間十分的平淡,並無看不起的意思,頓時目光微凝,隱隱側目。人生若隻如初見,他定然不會拿著那一幅紅梅圖,以她做局,誰能想到最後深陷局中的是他自己。
兩人在前方的遊廊岔路口分開。
秋長歌往南,蕭宣往西院。
他站在遊廊後駐足未走,就見她慢悠悠地打著團扇,帶著小丫鬟往心齋的方向走去,夜色中有高大勁瘦的身影疾步行來。
蕭霽一身黑衣,頭髮還是潮濕的,從心齋的方向大步流星地走來,許是剛回府,隻來得及去沐浴更衣,連頭髮都沒等幹就出來接人。
秋長歌見到他甚是驚訝,問道:「雪鴞不是說你今日不能回來嗎?」
「晚上還要出去,先回來看看你。累不累?」蕭霽接到人,心情雀躍,嘴上問著她累不累,沒等她回答,就將人打橫抱起來,抱著她纖細柔軟的身子,生怕她多走一步路。
秋長歌微微一驚,雙手環住他的脖子,小聲道:「還在外面,你這是作甚。」
蕭霽低低地笑,抱著她徑自朝心齋的方向走,兩人身影很快就消失在夜色中。
蕭宣神色未明地站在遊廊邊,覺得夜間的風,很是寒冷,吹的人心寒。
原來那樣狠辣無情的人,也視她如珠似寶,也懂她的珍貴之處,如今外面天翻地覆,他依舊抽空回來隻為了看她一眼,怕她累著,幾步路都要抱著她。
蕭宣覺得,他還是外出遊學吧,家中待著有些不是滋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