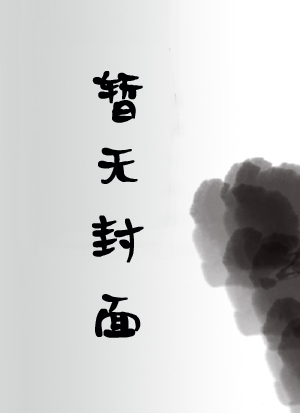第126章 情話多說一遍,我就會當真
鐵甲衛黑壓壓地站在庭院內,空氣中瀰漫著一股肅殺之氣。
周家二姑娘和錢四姑娘瑟瑟發抖地擠在一起,想起來時路上,她們不僅蹭了監國大帝姬的馬車,在馬車上逗弄幼帝,還聒噪地聊了一路,頓時嚇得臉色蒼白。
傳言攝政王殺人不眨眼,麾下的鐵甲衛出行,所到之處從不留活口,她們該不會就要死在這裡吧,嗚嗚嗚。
兩人弱弱地躲在穆青衣身後,隻見光風霽月的青衣居士神情十分地平靜,絲毫沒有慌張之色。
蕭霽俯身替長歌系好披風,撫了撫她鬢角的髮絲,然後擡眼,鳳眼冰冷地看向穆青衣:「穆小郎君,你回盛都,穆尚書知道嗎?」
穆尚書?周家二姑娘和錢四姑娘聞言花容失色,是那位權臣穆尚書嗎?青衣居士竟然是穆家郎君?那是盛都一等一的高門。
她們原本自傲自己的容貌家世,對穆青衣驚為天人之後多次糾纏,路上遇到秋家姐弟兩,也是毫不避諱地八卦,言語中都透著高高在上,結果這些人身份一個比一個尊貴,兩人被打擊的體無完膚,又驚又懼。
穆青衣不卑不亢地說道:「不勞攝政王大人費心,家父性情高潔,喜愛蘭草,青衣在山間無意尋到了一株鴉雪蘭,正準備帶回穆家。」
蕭霽鳳眼微擡,眼底有殺氣一閃而過:「小郎君回盛都也有數月,數次過家門而不入,隱居在深山,穆尚書知道隻怕會心寒吧。」
兩人言辭之中針尖對麥芒。
周二姑娘和錢四姑娘嚇得花容失色,覺得那些鐵甲衛手中的刀都要拔出來了。
「還讓不讓人好好吃飯?」
對峙中,一直沒出聲的大帝姬冷淡開口,聲線如玉質,悅耳動聽,透著幾分的淡漠。
蕭霽收回視線,揮了揮手,鐵甲衛快速地搬來桌椅,送上一道道精緻的菜肴,一邊是簡陋的石桌石凳,上面隻有幾盤素齋和一碟子蒿子粑,一邊是厚重的沉香木桌椅和十二道精緻可口的宮廷菜式。
對比鮮明。
周二姑娘和錢四姑娘面面相覷,帝姬肯定會選擇攝政王大人的晚膳吧!
長歌夾了一筷子素齋,吃了幾口,覺得酸辣下飯,都是她沒有吃過的口味,確實很好吃。
「兩位娘子,坐下一起吃嗎?」
周二姑娘和錢四姑娘猛然被叫到名字,嚇的小臉煞白,結巴道:「殿下,我們,我們不餓。」
長歌濃密卷翹的睫毛微斂,手指敲了敲桌面,面容冷淡且威嚴,兩人腿一軟,條件反射地坐下來。
飛章看了看阿姐,看了看太傅,又看了看笑的比哭還難看的兩位娘子,仰頭說道:「穆家哥哥,我還能再吃一塊蒿子粑嗎?」
「不能,你今日已經吃了很多了,小心回去鬧肚子。」
長歌敲了敲小傢夥的腦袋。
幼帝雙眼淚汪汪,委屈巴巴地說道:「好的,阿姐。」
又萌又軟。
周二姑娘和錢四姑娘見大帝姬和幼帝的相處日常,竟然如此可愛,猶如尋常人家感情深厚的姐弟,頓時沒有那麼害怕,覺得親近了幾分。
傳言中手段狠辣的監國大帝姬也隻是一個性格冷淡,沉默寡言的漂亮娘子,幼帝也根本不是癡傻兒,而是呆萌的小郎君。果然傳言都是不能信的。
兩人見長歌似乎沒有降罪的意思,又見氣氛尷尬,壯著膽子問道:「殿下出行,為何不帶鐵甲衛?盛都,盛都還是很危險的,尤其是對您和幼帝這樣漂亮的姐弟來說。」
長歌淡淡說道:「盛都若都是如此危險,那便是我和攝政王大人的無能。」
見兩位娘子一副要哭出來的模樣,她淡淡說道:「與你們無關,大盛積弱已久,我也隻是想想古籍上記載的夜不閉門,路不拾遺的光景。」
一時無話。長歌靜靜地吃完晚飯,吃的都是素齋,對蕭霽帶來的精緻菜肴碰都沒碰。
一頓飯吃的周二姑娘和錢四姑娘心驚肉跳,等到大帝姬吃完,攝政王蕭霽才帶著黑壓壓的鐵甲衛護送兩人離開。
兩人看著那位殿下的背影,久久回不了神。隻覺得這一日的經歷說出去不會有人相信。這位帝姬殿下帶給她們的震撼遠遠地抵消了她們被穆家郎君拒絕的痛楚。
不張揚不肆意,很是沉默安靜,那位殿下眼眸半闔,偶爾眼波流轉間就是無盡的風華,像是九天攬月,遙不可及。
她與權傾朝野狼子野心的攝政王大人分庭抗禮,讓不沾塵世的青衣居士三面傾心,讓滿朝文武對她恨之入骨卻無可奈何。
做女人做到這份上,才是真正的精彩。
兩位小娘子內心隱隱激動,覺得情愛都是浮雲,她們也想活成帝姬這樣,掌握自己的命運。
周二娘子見那些鐵甲衛盡數離開,忍不住問道:「剛才殿下吃的都是素齋,郎君為何不言語?你莫不是因為她是監國大帝姬,被她惡名所累,就嚇退了吧。」
穆青衣看著那碟子吃完的蒿子粑,溫潤一笑:「不,我在想,清明已過,蒿子粑是時令點心,等到端午,該做荷葉蓮花糕了。」
「你該不會以為帝姬會被你做的這些糕點打動吧,她身邊聚集著大盛朝最優秀的郎君,你看攝政王大人緊張的模樣,帶著那麼多的鐵甲衛,巴巴地從盛都趕來,哎呀,你真是榆木疙瘩腦袋,我跟錢四之前怎麼會喜歡上你呢。」
穆青衣微笑,目光深邃地看向下山的地方,笑容一點點地消失,那裡有火把明亮,猶如一條銀龍,蜿蜒地遊走在山間,照亮漆黑的夜。
父親書信上說,監國帝姬秋長歌是秋家最冷酷心狠的女人,是一個會毀掉大盛朝的女人,需除掉,那人給他的書信上也說,盛都危急,需要他返回盛都,撥亂反正,可他看到的隻是一個疼愛幼弟的小娘子,一個觀雨時冷漠,吃飯時安靜,被表白時都不會微笑的小娘子。
歲月是如何一點點地將她雕刻成這樣的?如果她微笑,那一定是天底下最可愛的小娘子吧。
三面入局,原來,他才是那個局中人。
長歌行走在山間濃霧中,看到穆青衣站在樸素寺廟裡,極目遠眺,看到周二姑娘和錢四姑娘跺腳嬌嗔,看到飛章攥著她的衣袖,睡夢中喊著阿姐,看到蕭霽神情冰冷地帶著她進入城郊的蕭家別院。
「帶陛下下去休息。」蕭霽冰冷的聲音傳來,大力揮開簾帳,猛然攫住她的手腕,將她壓在軟塌之上,眉眼隱怒,一字一頓地問道,「那個穆青衣。你喜歡他。」
是肯定句。
她後背撞在軟塌上,隱隱吃痛,神魂歸位,擡眼便看到了蕭霽眼角赤紅,眼中的殺意和陰鷙猶如烏雲沉沉地壓下來:「秋長歌,你敢!」
她忽而輕笑,低低地說道:「蕭霽,我敢呀。」
她低低地笑,笑容有些瘋狂,她有什麼不敢的。
蕭霽鳳眼陡然暗下來,無一絲亮光,許久,低沉沙啞地說道:「你不該破壞遊戲規則。」
對方伸手捂住了她的眼睛,冰冷且炙熱的薄唇狠狠地壓下來,無情地碾著她柔軟的唇角,窗外閃過一道驚雷,暴雨傾盆而下。
她打了他一巴掌,卻換來更粗暴且炙熱的對待。
極度混亂的一夜,山間的桃花盡數被打落,窗戶被山風吹開,落入滿室荒涼的雨,有幾瓣零落的桃花被風卷進來,落在簾帳內,她想,桃花開盡了,春天走了,不會再來。
此後一年,攝政王以大帝姬身體不適,需靜心調養,圈禁深宮,引得朝野震動。而深宮內,人人都知曉,攝政王時常歇在帝姬的朝華殿內,就連幼帝都不得近身,獨佔欲驚人。
*
帝都。
陸西澤猛然驚醒過來,掌心皆是冷汗,幾縷碎發淩亂地垂下來,俊美冷漠的面容帶著幾分的震驚和晦暗。
「陸總,還沒到別墅。」文理見他驚醒,神情陰鷙,聲音都不自覺輕了幾分,「您睡了二十分鐘。」
才二十分鐘?陸西澤看著外面浮華的京城夜景,他在夢裡像是渡過了一年,而且是那樣極度旖旎和悲涼的一年。
夢裡,零落的桃花,明艷且冷漠的美人,他喜歡看她坐在殿內批閱奏摺,一邊教著她如何制衡朝野,一邊吻遍她雪白的肌膚,像是一場百玩不厭的遊戲,一遍遍地沉溺其中。
他忘記了蕭家祖訓和仇恨,隻想撕碎那個冷漠美人的所有盔甲,讓她在他身下一點點地綻放,可從始至終,她都冷靜的,猶如捂不化的寒冰,冷眼看著他,然後不動聲色地吞食著他的勢力。
他也樂得讓她強大,這樣更能激發他的慾念和佔有慾。
陸西澤伸手按著突疼的太陽穴,聲音沙啞:「秋長歌呢?」
「秋小姐回莊園了。」文理低聲說道,秋長歌真的狠,不僅將陸總送的人魚之淚捐出去,還找宋星河來擡價,硬是逼著陸總掏了五十億。
今日之後,陸總在帝都想低調都低調不起來。
是了。慈善晚宴一結束她就離開。
陸西澤鳳眼幽暗,想起夢中發生的一切。如果夢裡發生的一切都是真的,那他們就是名正言順的夫妻。他不會放手的。
*
「長歌!」溫和充滿力量的聲音穿過層層迷霧,將她從夢魘中拉出來。
長歌猛然睜開眼睛,身上的毯子滑落在地,傅懷瑾清俊斯文的面容出現在面前。
「你剛剛出了好多的汗,是被夢魘住了?」傅懷瑾遞給她一塊柔軟的紗布,皺眉說道,「你時常做噩夢?」
她低頭看自己的掌心,發現掌心都是冷汗,指尖深深掐住掌心,留下數道紅痕。
見她斂眉不說話,神情冷漠的模樣,傅懷瑾心口微緊,一言不發地幫她擦了擦額頭和掌心的冷汗,然後取來藥箱,給她的掌心上藥。
「烤紅薯熟了,要吃一點嗎?」絕口不提夢魘的事情。
長歌回過神來,被壁爐的火一烤,身體暖了幾分,又見傅懷瑾搬來了一個小火爐放在身邊,頓時低啞地問道:「我睡了多久?」
「大約二十分鐘,正好爐子裡的紅薯烤熟。」
原來隻用了二十分鐘,她卻像是過了一輩子那麼長。
傅懷瑾給她倒了一杯薑茶。
她喝了一口,潤了潤乾裂的唇角,見他拿著手術刀救死扶傷的手,幫她剝著紅薯,頓時心尖一軟,低低問道:「傅懷瑾,你覺得我如何?」
傅懷瑾手中動作一僵,許久,剋制地說道:「很好,像是上輩子就見過的人,一見如故。」
她微微一笑:「那等我離婚,我們就在一起吧。」
傅懷瑾渾身緊繃,見她明明是笑著,眼裡似有無數細碎的傷口,明明是那樣溫暖的話,她說時沒有歡喜情愛,沒有動情,亦沒有歡欣雀躍。
他忍不住伸手,想撫摸她柔軟的髮絲,手停頓在半空,終是克制地收了回來。
傅懷瑾溫潤笑道:「這樣的話,我會當真。」
長歌定定地看著他,視線滑過他的英氣的眉毛,溫潤如深海的眼眸、高挺的鼻樑以及優越的下頜線,第一次這樣認真地看他。
傅懷瑾這人,長得十分的光風霽月,一言一行都讓人無比的舒服,像是一塊圓潤沒有稜角的暖玉,他有在乎的人嗎?有過瘋狂的愛戀和無法忘卻的人和事嗎?
「你性格一直這樣?從未大悲大喜過嗎?」
傅懷瑾唇角的笑容微斂,許久說道:「我生來便是這樣,無名大師說,我還沒有遇到那個讓我生出眼角淚痣的人,得修無數的因果,攢無數的福報,才能換來來世的短暫一面。」
長歌聞言嗤笑:「原來是個騙子,他是不是想誆你出家?」
傅懷瑾見她眉眼舒展開來,笑道:「被你看出來了。若是無名大師看到你,沒準就會放棄我,改為遊說你了,你看起來慧根很深。」
長歌:「我前塵往事糾葛極深,這輩子註定要困在心魔之中,不過能聽著山間的鐘鳴聲,沒準能早日擺脫心魔。」
「紅薯熟了,可以吃了。」
兩人絕口不提之前的那句無心之語,吃著烤紅薯和甜酒煮蛋,聊著一些平日裡不曾深聊的佛理道家學說,直到夜深。
長歌沒有回莊園,烤著火,睡在橙園客廳的沙發上。
傅懷瑾看著她熟睡的睡顏,替她蓋上毯子,輕輕撫平她皺起的眉尖。
他想,他已經遇到了那個讓他生出眼角淚痣的人。